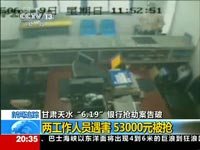6月23日,山西副省長劉維佳再訪溫莊。中午,在村民的院子里,一群官員陪著劉維佳在吃午飯。手搟面,十多個剛煮好的土雞蛋,土豆絲、蔥拌豆腐和涼拌黃瓜。山西省財政廳副廳長突然問山西省農發辦主任,你在農業口工作了30多年,吃過幾次這樣飯?農發辦主任答,吃過2次,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1986年,是在農民家炕頭吃的。(據6月24日《新京報》)
劉副省長的《沁縣溫莊下鄉住村筆記》本來是省委省政府布置的作業,原文7千多字,人民日報摘要發表也發了5千字。這樣的駐村筆記就像山西省農發辦主任吃的農家飯一樣,30多年才吃過2次,十分“珍貴”又“動人”。
從4月26日劉副省長自帶被褥來到溫莊至今,短短2個月這里變化巨大。如今,溫莊的“噴灌工程”已修好,田地已澆過兩遍。沿村道的民房被統一刷成了白色,部分墻面寫上了“發展特色產業實現收入翻番”的標語。育苗基地已定址。核桃園已經做好規劃,等秋季收割后開始種植。養殖園區也初步選好了地方。田間路也將修好。……由此,完全可以預想,溫莊很快就會出現奇跡,富裕和幸福不日即來。
副省長到訪后,60歲的溫莊村支書霍敬德忙了起來。各級官員到村里的頻率,明顯比過去高了。他說,這是他第一次面對面見到副省長。當村官十多年,之前他見過的最大的官是前任縣委書記。我們的官員真是太忙了,忙得只剩下了溫莊那副牛耕人種的“農耕圖”:種田人是62歲的老年夫婦和嫂子。有農機不肯用;有水源不能澆;有真話不敢說。副省長不來,這里一片荒涼,一來,就成了“集鎮”。無疑,這十分幽默,只不過是讓人笑不起來的黑色幽默。
其實,領導駐村的所見所聞,其主題就是“三農”問題。有關“三農”的ABC、一二三,既有專家理論,又有網帖播報。這些年來,中央一號文件關注的還是“三農”,“三農”的確在變化,種地有了補助,只賺不賠。可是,也要看到,種地的賺頭還是太微太小,留不住人。不久前筆者回老家幫父母麥收,看到機械化帶來的背后,是汗水、勞碌和辛苦帶來的不協調收益。就是收割機手,他們也是身心疲憊,令人同情,不敢向往他們的發財門路。
只不過,溫莊就是溫莊,溫莊問題并不能復制。這些問題多年來就被官僚和城市化當做“沉默的聲音”,沒人打撈,沒人傾聽,更沒人操心。城市多美好啊,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富麗堂皇,吃喝玩樂到處都是一條龍。城市化的旋律里暴漲來的財富,年年翻番都嫌慢,恨不得天天翻番。所以,拆遷、建設、工地的海洋,然而在水泥森林里制造景觀,不夜城里,每個人都像吸血的蚊子,仿佛生命就是那樣開花那樣結果,才是終極目的似的。
還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對,中國的問題其實就是農村農民問題。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是百業之母。農村不能凋敝,農民不能窮困。不然,即便城市再耀眼,也不過像鬼市一樣,天一亮,一切都是子虛烏有聲跡皆無。這個天,就是溫莊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