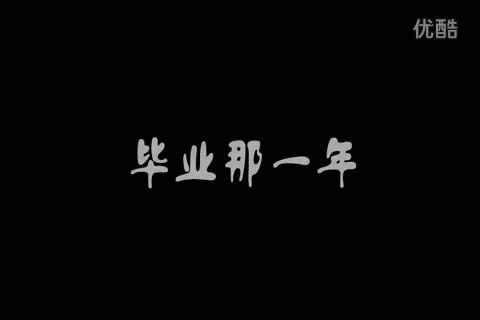正是由于公路收費對于地方政府巨大的重要性,在應對來自上層的各種整治政策時,地方政府往往會通過各種手段化解具體的政策。全國政協委員宋振鐸曾透露,北京機場高速到2005年收費總計32億元,但實際上,這條建于1993年的高速公路造價不過11.65億元。建立之初,北京機場高速施行“還貸收費”,收了3年多后,又轉為經營性公路,這樣就在1997年1月得以重新批準收費30年,估算到收費期滿的2026年底,還能收費90億元。類似的情形在各地并不鮮見,諸如廣州花都區五個收費站在沒有年檢的情況下持續收費多年,甚至經營該公路的公司還存在高官背景等。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領域是一個利益博弈的場所,公路的收費政策涉及利益巨大,更是充斥了各方利益主體的搏斗。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整治亂收費情況,可地方依然照收不誤,其重要原因在于目前有關收費公路的信息不夠透明,這就導致了公眾和媒體的監督無法直接介入。然而,對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員而言,身處政府系統的他們對于具體政策關鍵點的理解,以及對于政策出臺步驟的熟諳,都遠甚于公眾。這使得在這盤利益博弈的棋局中,真正的成本擔負者———公眾則只能置身一旁、隔岸觀火,靜靜等待自己命運的落定。
在具體的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哪一個利益相關方缺席,該利益主體就必定遭受損失。此次五部門的聯合行動盡管態度堅決,也高調強調除了清理收費站外,還要完成地方性法律法規的規范和收費公路的信息公開工作。但總體而言,如果公眾在公路是否收費、該收多少費的政策制定上繼續失聲,一旦地方上的利益集團展開利益博弈,這依然會是一出與公眾完全無關的老戲碼。因此,對于公眾而言,必須取得在公路收費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話語權,包括通過聽證會表達意見,要求收費公路公開收支情況和余款使用情況等。只有公眾的目光得以介入,公眾的影響才得以發揮,公眾的利益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