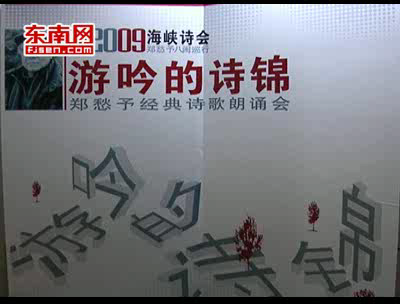積累和消費的平衡,在農業建設領域具體表現為處理好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毛澤東反對蘇聯那種以損害農民利益來獲得經濟建設積累資金的政策,主張通過實行較低農業稅,采取縮小工農剪刀差以及提高農產品收購價等政策來保護農民的經濟利益。他指出,農業是積累的重要來源,農業發展起來了,就可以為發展工業提供更多的資金,但是,農業本身也需要積累。“農業本身的積累和國家從農業取得的積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為好?請大家研究,議出一個適當的比例來。其目的,就是要使農業能夠擴大再生產,使它作為工業的市場更大,作為積累的來源更多。先讓農業本身積累多,然后才能為工業積累更多。只為工業積累,農業本身積累得太少或者沒有積累,竭澤而漁,對于工業的發展反而不利。”他還指出:“合作社的積累和社員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價值法則搞經濟核算,要勤儉辦社,逐步增加一點積累。”毛澤東還把積累看成是一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相應調整的過程。他說:“今年如果豐收,積累要比去年多一點,但是不能太多,還是先讓農民吃飽一點。豐收年多積累一點,災荒年或半災荒年就不積累或者少積累一點。就是說,積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6]200
三、毛澤東合理分配思想的當代啟示
縱觀毛澤東的社會分配思想,在反對平均主義和“過分懸殊”之間,主要傾向是反對“過分懸殊”。在毛澤東時代,我國社會分配的基本格局是“公平(均平)優先,均中求富”。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客觀上看,中國貧窮落后的國情和計劃經濟的體制限制了分配差距的拉開。在經濟增長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間,毛澤東原來希望既能多、快、好、省地推動經濟增長,又能迅速使老百姓擺脫貧窮,但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遭受的嚴重挫折使毛澤東認識到,“趕超式”的經濟發展并不可行,中國的工業化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甚至需要100年。因此,在有限的社會消費品分配中,也只能是“公平(均平)優先,均中求富”。
主觀上看,毛澤東在內心深處對于社會分化保持警惕,他不愿意看到分配中出現“過分懸殊”、“兩級分化”等現象。他認為這些現象是與社會主義制度背道而馳的,體現的是資本主義自發傾向,最終將導致資本主義。因此,在毛澤東晚年,無論是對農村中“包產到戶”,還是對企業中“八級工資制”,凡是有可能助長“個人主義”、導致差距擴大的做法,他都心存疑慮,予以批評。1974-1975年期間,他多次談到中國雖然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都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他引用列寧的話說,我們自己建設了一個“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國家”,分等級,搞等價交換,保護了資產階級法權,實行的是不平等的制度。由此可見,以按勞分配為核心的合理分配機制之所以沒有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這與毛澤東本人對中國實踐按勞分配制度認識上的變化和反復有著密切關系。
|
|